同治《大邑县志》校注
发布者:
责任编辑:王斌
发布时间:2023-12-19 23:17: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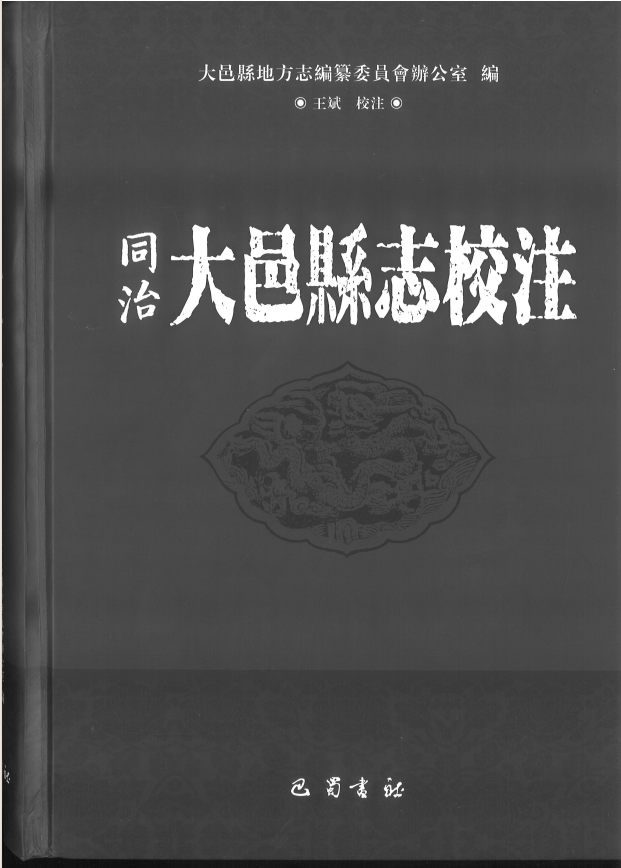
同治《大邑县志》,由赵霦等人于同治六年(1867)年修成,共20卷。清人林嘉澍、余上富等,依同治原本略加剜改、增删而成光绪二年(1876)修订本,但此次改动不大。虽然《中国地方志集成》及国家图书馆方志库皆著录修订时间为1876年,但其书卷八实有光绪三年事。四川大学图书馆藏有在修订本基础上增补重印的增订本,具体增订时间不详,记事最晚亦为光绪三年,但新增内容较多。此次整理,即以川大图书馆所藏增订本为底本,参校国家图书馆藏光绪二年修订本及同治六年原本。整理时,施加新式标点,对一般文史典故进行注释,尤其是对金石、艺文部分做了大量校注工作。同时尽可能覆覈引文,纠正了原书存在的不少错谬。由于诗文散见于金石、艺文及人物传记,故书末附诗文篇名目录。该书分获乐山市第十八次社科奖二等奖、四川省第十九次社科奖三等奖,已被中华经典古籍库全文收录。
附:《同治大邑縣志校注》序
在今天這個比較浮躁、功利的時代,如何實現效益最大化似乎是人們最樂於談論的話題。只有深刻認識到中華文化的巨大力量以及所賦予我們的神聖使命的人,才能夠沉下心來去做那些在世人看來費力不討好,又没有巨大經濟效益,并且是艱苦細緻而又瑣碎的工作。古書的校注就屬於這樣的工作。
古書的校注在清朝的乾嘉時期達於頂峰。那個時候古書校注基本上可以等同於漢學(也可以稱爲樸學,漢學是從師法漢代人治經學的角度講的,樸學是從具體的方法上講的),漢學運用的主要武器就是校注古籍,是那個時期有真才實學的大學問家的標志。産生了如顧炎武、閻若璩、朱彝尊、惠棟、戴震、王鳴盛、錢大昕、畢沅、江藩、王念孫、孫星衍等一大批大家。但隨著清朝逐漸走向衰落,特别是清末中國處於積貧積弱和外强入侵的悲慘境地的時期,一些學者把乾嘉時期漢學的興盛簡單地歸於清朝統治者文化鉗制政策在士大夫身上的反映,或者説這些士大夫們是爲逃避現實而鑽入象牙塔,從而大加撻伐。當然,漢學本身確也有趨向瑣碎、掉書袋似的尋章摘句,以及不能直接解決現實問題(即所謂經世致用)的現象,因此,這個時候一部分士大夫痛感漢學不濟時勢又重新拾起了與之長期對峙的宋學(宋學,兩宋理學家治經學的統稱。主要是運用闡釋的方式解經,而不斤斤於文字本身,具有比較明顯的主觀色彩。如果説漢學是“我注六經”,那麼宋學就是“六經注我”)。特别是到了戊戌維新時期宋學佔據了主導。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更有一部分激進的學者既否定漢學也否定宋學,以致全面否定傳統文化,或者完全用西方的學術方法學術思維來釋讀中國的古籍。更有甚者認爲,中國傳統學術不能稱爲嚴格意義上的學術,要研究中國古典文化需要到外國去學習如何研究,真正有邯鄲學步的意味,正如錢鍾書在《圍城》裏所諷刺的一樣。在這樣一個一邊倒的背景下,仍然有少數人在默默無聞地堅守自己的信念,塌下心來繼續從事古籍校注的艱苦工作,并取得了巨大成績,出現了像范文瀾的《文心雕龍注》,王利器的《新語校注》《文鏡秘府論校注》《顔氏家訓集解》,高亨的《周易古經今注》《周易大傳今注》,余嘉錫的《世説新語箋疏》,周祖謨的《洛陽伽藍記校釋》,張大可的《史記全本新注》等等一批現當代名著!但畢竟是少數人!今天甚至相當一部分學習古漢語專業的人也不會熟練地運用傳統的方法校注古籍,古籍的校注工作面臨如何接續與傳承的問題!
隨著改革開放四十年所取得的天翻地覆的進步,中國又重新站在了世界舞臺的中央。我們從切身的實踐中體會到了不能不走自己的道路,不能不從中華文化中汲取智慧,不能不發出體現中國自身特點的聲音!正是從這樣一個新的高度來反思一百五十多年來對古籍的校注,發現我們過多的看重西方闡釋學的方法的移植,而没有深刻地思考我們傳統校注方法的針對性及其價值、意義,也就是説只有用中國思維方式所産生出來的話語表達來校注中國古籍才是對路的,即使是借鑑西方的方法,也必須消化後轉化爲我們的方式才行。傳統的音韻、訓詁、文字學和義理、考據、辭章相結合的方法,在今天看來仍然是校注中國古籍、解碼中國傳統文化的圭臬。今天在經歷了這麼多的經驗與教訓後,在全球化大時代的國際交往中終於發現,我們的文化是如此具有歷史的穿透性,完全可以給世界提供中華文化的智慧!完全可以爲世界建立起一座豐碑!而浩如煙海的中華古籍就是這個豐碑的有機組成部分,我們校注的每一本古籍就是這個有機組成部分的一磚一瓦!所以古籍校注工作是一項偉大的工作!
正是因爲這是一項偉大的工作,正因爲這是需要我們一代一代人接力的工作,所以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是值得尊敬的!這項工作需要心靜,需要不怕麻煩的耐心,需要擯棄世俗的輕視的目光,更需要扎實的學問。對於舊志,我歷來的觀點是首先影印,然後才是校注。影印是爲了搶救與保持古籍原貌,也是爲了避免歷史上屢次出現的每翻刻一次就錯誤增多一次的情况。而校注,尤其是舊志的校注,我認爲需要有大學問,不是一般人能夠承擔得了的,因爲有些人雖然有專業的訓練,但除了一般性的校注字句外,由於對當地的風土人文和歷史底蘊不甚瞭解而出現郢書燕説以至於魯魚豕亥,所以,我一直提醒區(市)縣地方志辦公室不要輕易校注舊志,一定要找真正的行家來做這項工作!事實上,過去成都各區(市)縣的舊志整理品質確實是參差不齊,水準普遍不高。偶有較規範的點校本問世,但也不敢在注上做文章。市本級雖整理了成都市區和原所屬附郭的歷代舊方志三十餘種,但仍然難免有深度不夠和個别錯訛情況的發生。所以,當我看到王斌先生主編的“巴蜀掌故五種校注”之一的《蜀都碎事校注》一書後,眼睛一亮,由衷的爲他所取得的成績高興!這本書的校注可以用“精良”二字來形容!全書僅徵引書目就近五百種,鉤沉群籍,考據清晰,辯證正誤,注釋簡明,要言不煩!正因爲如此,當大邑縣地志辦讓我爲王斌先生校注的《同治大邑縣志》寫個序的時候,便欣然接受了。《同治大邑縣志》纂修於清同治六年,光緒二年又有所增補,應該説雖然不是一本精品力作,但仍然具有鑑古知今的傳世價值,特别是對那個動盪歲月老百姓的生活以及基層士大夫的狀况都有比較詳實的記述,并且保留了一部分珍稀的碑刻藝文。關於這本志書的具體情況,王斌先生在前言裏已有詳述,在此不再贅言。書我看了一部分,風格與《蜀都碎事校注》一書一致!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這是一本好書!是爲序。
高志剛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九日